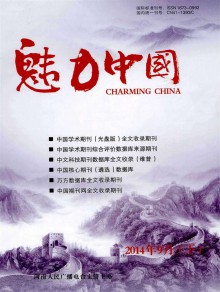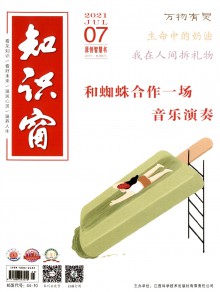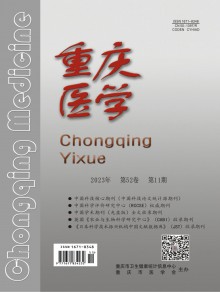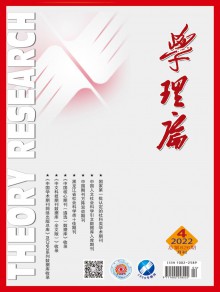外耳道副耳伴第三鳃裂瘘1例
时间:2025-04-07
叶伟龙,孙 波
(1. 大连医科大学 研究生院,辽宁 大连 116044;2.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口腔颌面外科,辽宁 大连 116023)
1 临床资料
患儿,女,22个月,家属诉患儿自出生即发现右耳外形异常,右颈部见一“针尖”大小瘘口,常有液体流出,无明显不适感。于2017年8月7日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就诊,查体见患儿面部表情肌运动自如,右耳屏形态异常增大,约1.5 cm×2.0 cm,右耳屏前可见一肿物,约0.2 cm×0.2 cm大小,触之软骨样感;右侧胸锁乳突肌下1/3前缘可见一“针尖”大小瘘口,有清亮液体流出,余未见明显异常(图1)。CT检查见右侧胸锁乳突肌上方低密度灶,考虑第三鳃裂瘘(图2)。以“右侧第三鳃裂瘘、右外耳畸形”收入院。排除手术禁忌,于2017年8月9日在全麻下行右耳廓畸形矫正术、鳃裂瘘切除术、口腔颌面小肿物切除术。术中患儿取平卧位,头偏健侧,切除畸形耳屏,去除软组织保留软骨,置入外耳道前壁组织间隙内,恢复外耳道外形;于右侧胸锁乳突肌前缘下1/3探寻瘘口,经瘘口注入亚甲蓝,沿颈部瘘口表面及颈线设计切口,切开皮肤、皮下及颈阔肌,钝性分离。沿亚甲兰染色,追踪瘘管,完整切除病灶及周围部分正常结缔组织(图3)。术毕切除物送病理。病理诊断:(1)(右耳前肿物)组织表面被覆鳞状上皮,其下为成熟的毛囊、皮脂腺及脂肪组织,诊断副耳。(2)(右侧第三鳃裂瘘管)纤维性囊壁充血、出血,被覆鳞状上皮及复层纤毛上皮,上皮下可见大量淋巴细胞浸润,符合瘘管病理改变,需结合临床作最终诊断。病理结果见图4。患儿术后恢复良好,于2017年8月14日出院。出院1年后随访,见患儿一般状态佳,术区恢复良好,无复发。
图1 副耳及肿物Fig 1 Accessory auricle and tumor
图2 术前CT示右侧胸锁乳突肌上方低密度灶Fig 2 Preoperative CT showed low density focus above right sternocleidomastoid muscle
图3 术中切除瘘管及正常周围结缔组织Fig 3 Intraoperative resection:Fistula and normal surrounding connective tissue removal
图4 术后病理示纤维囊壁充血,被覆鳞状上皮和复层纤毛上皮,大量淋巴细胞浸润Fig 4 Postoperative Pathology showed hyperemia on fibrocystic wall, covered by squamous epithelium and stratified ciliated columnar epithelium, with massive infiltration of lymphocytes
2 讨 论
副耳是较为常见的外耳道畸形,单侧患病率约为1.7∶1000,双侧患病率约为9~10∶10000[1],一项在中国的调查结果显示流行病学发生率约为0.22%,而在土耳其的调查结果约为0.45%[2]。部分患者具有家族聚集性,为显性遗传,可单发或多发,可局限于单侧或同时发生于双侧[3]。临床表现为除正常外耳廓以外,副耳可见于耳屏前与口角连线的任意部位,颊、颈部等,突起的皮赘颜色与正常皮肤相近,但数目形貌不一,下可扪及软骨成分,形似小耳廓,病因与耳丘融合不全有关,本质来源于第一鳃弓异常发育[4]或第二、三、四鳃裂的软骨结构不良[5]。同期可能伴随其他颌面部畸形,如本病例中的右侧耳前小肿物、第三鳃裂瘘,但相关度及其原理仍需进一步探讨。赘生的软骨同主耳软骨可相连或分离,向内可以延伸至颊部,通常不影响机体的功能。但除患者主诉的美学问题外,亦可伴中耳或内耳的听力异常,因此有必要进行相关的功能检测。副耳常局限于特定部位,也可为多种遗传性综合征的标志,如Branchio-oto-renal综合征[6],Goldenhar 综合征,Townes-Brocks 综合征, Treacher-Collins 综合征, VACTERL 综合征, Wolf-Hirschhron 综合征等[7]。本病例患儿查体、CT及病理表现为右侧副耳、右侧第三鳃裂瘘,未见有泌尿系统及其他系统畸形,借此得以鉴别各类综合征。
鳃裂在胚胎3~8周发育形成颌面部的同时逐渐退化,若退化不全穿通皮肤则形成窦道;若窦道开口至梨状隐窝则称为鳃裂瘘;若鳃裂上皮残余但未穿通,则形成囊肿[8]。第三鳃裂囊肿好发于颈根部、锁骨上区,若有外口则常位于胸锁乳突肌下1/3前缘,沿颈阔肌深面顺颈鞘向上,伴随迷走神经,依次绕过舌下神经、舌咽神经、茎突咽肌、颈内动脉,穿过甲状舌骨膜,内口开口于梨状隐窝[9]。相比诊断第三鳃裂瘘,第三、四鳃裂畸形的鉴别相对困难,常被共称为梨状窦瘘。有学者回顾了72例第三鳃裂畸形患者的组织学表现,其中58%含有复层鳞状上皮,35%含有呼吸道纤毛上皮,40%含有胸腺组织,19%可见甲状腺组织,10%可见甲状旁腺组织[10],但临床中仍难以作为两者之间的鉴别依据。由于第三鳃裂瘘临床较少见,易继发感染、反复肿痛,进而因误诊致疾病迁延、切除不净[11],故家属述患儿反复发生颈旁感染时,医生需考虑第三、四鳃裂畸形的可能性。第三鳃裂瘘于急性期可有脓肿,发热,疼痛,水肿,皮温等表现,而非急性期可无明显症状;若窦道、瘘管开口于梨状窦,则可伴有呼吸系统综合征,吞咽疼痛或困难等[10]。本例患儿无明显不适,只可见颈部瘘口,有清亮液体渗出,故判断未处于急性期,可行手术治疗。
副耳不影响美观可暂不处理,但若患方要求也可行手术切除。对于第三鳃裂瘘,术前CT、MRI、超声等检查有助于了解病变的位置和范围。术中应当彻底切除瘘管全程及内外瘘口,残存上皮极易复发。反复感染易导致炎性渗出、粘连甚至恶变,故需积极抗炎治疗。术中活检和手术切除尽量一次完成,以免瘢痕组织增生,增加再次手术的难度。瘘管与颈鞘,舌咽神经,迷走神经等重要解剖结构临近,术中应注意加以保护。为正确定位瘘管,可于瘘口逆行注射亚甲蓝,再沿染色追踪瘘管,于染色区域外缘分离瘘管及周围上皮组织彻底切除。术中牵拉瘘管时用力不能过大,以免拉断瘘管致残余组织种植、断端难以找回。如追踪到瘘管内口,在此可结扎瘘管根部并切除。如疑有发生恶变则需术中冰冻送病理观察,必要时追加颈淋巴结清扫术等术式。
综上,副耳与第三鳃裂瘘同为颌面部发育畸形,副耳相对较为常见,而第三鳃裂瘘则相对罕见。患儿的副耳位于外耳道,原因可能为第一鳃弓的耳结节融合不佳,而第三鳃裂瘘则可能为第三鳃裂退化异常。两种畸形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延续性,相关度如何,或只是同时共存,这些疑问目前仍未得到解答。以目前文献检索所见,此两种发育异常同时见于同一病患相当罕见,相关颌面部发育畸形的研究,仍需对类似病例进行更深刻的探索。
免责声明
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,注重分享,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,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,或有版权异议的,请联系管理员,我们会立即处理!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,内容仅供学习参考,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!